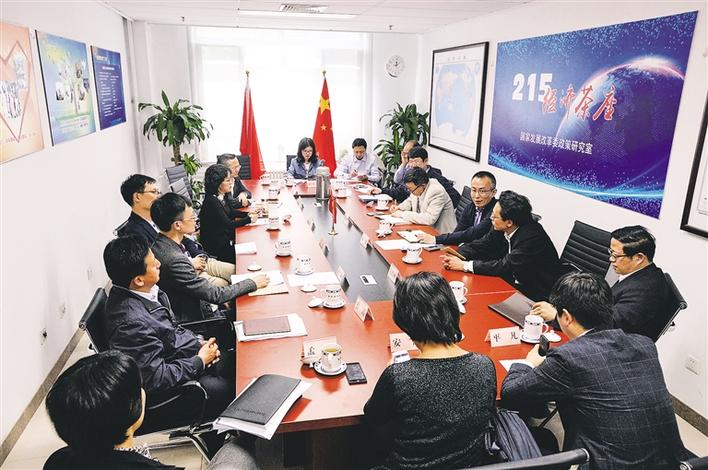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正式亮相,第一期聚焦“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胡鞍钢、王昌林、祝宝良、吴晶妹、许伟、张斌等专家学者与国家发改委部分司局长共议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上的新机遇、新观念、新作为
□ 本报记者 徐 赟
春风拂绿。4月17日上午,北京月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南楼215会议室高朋满座。由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发起、与综合司联合主办的第一期“215经济茶座”在这里举行。举座畅议,历时三个半小时。
怎么更好地“抓宏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改委对这一重大课题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215经济茶座”即在这样的思考与探索中应运而生。它将经常邀请社会上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与国家发改委的司局长等直接从事一线工作的政府官员,围绕重大主题,展开坦诚交流、专业研讨。在“215经济茶座”的前期筹备期间,何立峰、宁吉喆等委领导都给予了具体指导。
第一期“215经济茶座”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国家发改委作为宏观调控和综合经济部门,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正是其职责所在。
集思广益,兼听则明。基于本期主题,国家发改委政研室、综合司邀请了六位知名专家学者,与委内多位司局长围坐一桌,一杯清茶,就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面临哪些新情况?”“工作中需要做出哪些转变?”等话题展开讨论。茶座主持人、中国改革报社副社长、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在开场白中讲了三个“真”——“真诚地请大家来,一起讨论真问题,期待收获真知灼见。”
六位专家学者是胡鞍钢、王昌林、祝宝良、吴晶妹、许伟、张斌。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严鹏程、副主任孙涛、副主任孟玮及综合司司长丛亮、财金司司长陈洪宛、价格司司长岳修虎等参加了讨论交流。
预期管理:政策协调性要强目标要明确 执行要有定力
预期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国内外不乏新探索。茶座的讨论,直接从这个“新”处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用好宏观调控的众多工具和手段,首先要明确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的进程,其实也是打破增长瓶颈的进程。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瓶颈,把这个瓶颈打开,经济就能一步步往前走。”他在作了一番国际对比分析后提出,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目前二三产业占比较低、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较低、城镇化率较低。“这三个现象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侧面,但背后原因是一样的,说明大量人口还停留在农村,不能有效进入到城市。为什么?城市公共服务不完善,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张斌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首要的、最迫切的是解决公共服务这个瓶颈,让农民在城市更好地安家生活。
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张斌以分析前几年我国较大资本流出和较强汇率货币贬值预期共存的经历为例,总结出几条经验。他认为,汇率放开和资本项目放开必须协调好,以避免出现政策“打架”情况。再如,在市场汇率升值预期情况下,引导形成贬值预期,当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时,贬值预期发生了“叠加”。张斌认为,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政策要更加注重协调,政策跟经济基本面也要注重协调,同时执行政策需要定力。“确定某个方向对,就应该坚持,不能遇到一点阵痛就退回来。保持政策定力,就是在稳定预期。”张斌说。
围绕宏观调控中的预期管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首先要明确调控的目标。政策跟目标之间一定要有相关性,总量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等要组合运用,以解决短期、中期、长期等不同周期长度的目标。在长期预期不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预期管理主要针对短期问题。“要让预期真正发挥作用,目标一定要研究确定好,但是确定这个目标本身是有难度的,并且还要放到长期发展目标下考虑。”祝宝良说。
他认为,目标确定后,不同部门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否则政策的公信力不够。同时,宏观政策要关注对微观领域的影响。例如,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具体到微观领域,就变成产业布局的利益平衡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对与不对”的问题。不同部门对政策的取向是不同的,必须有统一协调部门才能解决问题。
再次,对于已经扭曲的政策,矫正需要加大力度,不妨“矫枉过正”。在这个前提下,行政手段是解决行政扭曲非常重要的办法。此外,要抓住主要矛盾,在集中精力解决重点问题的过程中,要保持定力。在政策效率提高之后,再调整下一步目标。
祝宝良认为,当前我们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高质量发展。未来宏观调控,需要有抓手。环境指标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许多政策工具都可以结合进去。在这方面,存在产业布局以及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决策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放开市场。此外,防控金融风险也可能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
大胆创造新工具:把大数据、信用等要素纳入调控
宏观调控的创新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茶座中的讨论,逐渐聚焦在一系列正在发生的“新情况”上——随着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业态、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需要作出相应转变。例如,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概念,而M2是重要的宏观调控变量之一。再如,网络消费等经济活动产生的大量数据,是否应作为公共产品纳入调控体系当中?
祝宝良表示,移动支付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它也使宏观调控的目标、物价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现金支付减少,移动支付体量迅速扩大。针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M0、M1、M2)进行调控,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政策。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祝宝良的分析表示赞同。他认为,宏观调控者要善于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目前很多私营公司的业务活动,实际上创造了很多潜在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公共信息,其数据覆盖面和细分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政府统计部门。要考虑如何利用好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掌握的数据产品,更客观地反映供求关系,为宏观调控提供新工具。此外,基于我国移动支付的体量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我国将可能在新技术、新经济方面对当前世界通用的计量框架完善做出贡献。
胡鞍钢提出,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是主要内容,但政府在这方面情况不够清楚,正好借助私人公司提供的信息来弥补。“因为我们更关注消费者是什么样的消费群体,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敏感的就是企业,它们能提供非常好的社会资源。”
信用管理是否也能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创新手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晶妹认为,目前整体网络支付的流量是银行最终登记的支付清算、结算量的几十倍,这个流量对经济的影响巨大。但对信用脱离货币运动的监管几乎是空白,对P2P平台的监管也亟待加强。
“联合奖惩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核心点,但这个核心点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活动不相关,那么我认为它最终不会落地。”吴晶妹表示,目前,信用建设方面的领导机制是国家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双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它解决了信用体系建设起步阶段的基本问题。“但是在高质量发展情况下,这是不够的。联合奖惩在很大程度上摸不到资源配置的核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终一定会停留在社会宣传、教育、社会治理的作用上。”吴晶妹说。
她提出建议,成立信用与大数据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把信用更好地运用于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探索建立信用资产交易所,让信用有能落地的市场。
在吴晶妹看来,在市场上有20家左右企业掌握大数据,拥有管理能力和权限,例如阿里、京东、腾讯等。“他们真正掌握独立的信用数据,我们应该想办法引导他们为国家服务。”吴晶妹说。
“企业愿意将自身掌握的数据用于国家宏观调控吗?”主持人杨禹问道。这也是许多与会者共同的疑问。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企业足够大就会愿意。”吴晶妹表示,当企业市场占有率足够、生存不成问题的时候,社会责任感就会凸显。事实上,这些企业已经对市场有影响能力,只是没有纳入政策当中。“如果跟政策结合绑定,它自身的调控更具预期性、更有战略性,它会更愿意。”
传统手段再创新:运用好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胡鞍钢常年跟踪研究国家发展规划。他认为,我国有不同于西方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让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幸免,同时还解决了自身许多问题,包括机构改革。他认为,我国有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三个宏观调控部门,此外还有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经济决策部门,这样的设置比较合适。中国还有特色的宏观决策机制,即会议决策机制,例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等,这些会议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机制。
胡鞍钢认为,从解决问题所对应的周期长度来看,国家五年规划和宏观调控是很好的结合。五年规划更加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强调战略目标,确保核心目标的实现,反映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宏观调控则相对着眼短期,服务于核心目标,并将之与当期目标结合起来。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概括,我们已经基本上形成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胡鞍钢认为,宏观调控体系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我国有国外没有的长期规划和目标;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本身也是创新,例如,我国把节能减排、空气质量等社会指标也涵盖其中;特别是,我国有全世界都没有的特色指标——城镇新增就业,而这一点与我国着力创造新增就业的国情密不可分。
对接宏观调控,胡鞍钢认为要运用和发挥好“两只手”“两条腿”“两个积极性”。“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条腿”,可理解为国企和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胡鞍钢认为,针对地方发展的分化情况,发展好的地方可以留足空间使之继续发展,重点对发展不够好的地方进行指导帮助。
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和注重“中国特色”相结合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许伟认为,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和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九十年代比较接近,同时我国目前整个政策,包括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也面临类似的调整和转型。“我们可不可以吸收他们的优点,同时又把我们目前着眼中长期、全局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结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分析了产业政策的创新完善。王昌林认为,我国产业政策到了转型的阶段,因为产业政策面临着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挑战。
从国际来看,一方面,全球产业竞争愈发激烈将成为长期趋势;另一方面,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正在打造比较完整独立的三角形产业格局,往中高端走,同时发展传统能源。
从国内看,国内的产业政策不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主攻方向还不够清晰,产业创新体系、基础创新体系还达不到要求,产业组织政策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融资、人才等方面都面临挑战。
对于学术界曾热议的“产业政策还要不要”的讨论,王昌林认为,第一,产业政策还是得要,但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而且要实,要有主攻方向。要跟国际接轨,表述上避免被曲解。第二,产业政策要向创新政策转型,组织政策主要是强化对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扶持。要强化竞争性政策,摒弃“选运动员”的方式,创造公平的准入环境,让运动员同台竞争。第三,要加快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要利用好庞大的内需市场,坚定不移往中高端迈进。同时,完善应对国际争端的政策法律体系。
胡鞍钢认为,我国产业政策恰恰助推了我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集。“我们不是简单地讨论政府和市场关系,或者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要关注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胡鞍钢说。
提升发改委履职效能:抓宏观 抓协调
结合国家发改委的宏观调控职能,许伟认为,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体系,基本适应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变化。
一方面,经济结构变化要求宏观调控进行调整。根据中长期研究,我国投资效率开始面临瓶颈,房地产和基建比重打破平衡,但公共服务存在短板。围绕消费的体系还没有建立,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分配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宏观调控者需更注重政策表述上的精准,注重准确进行预期管理。
许伟提出建议,第一,目标的多元化要求政策更协调。“一个工具箱里面,目标和工具应该相匹配,切忌监管竞争,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第二,更精准的微观手段调节,还是让给市场调节,政府用间接的、法治的手段调节。第三,抓好重大战略、政策和项目的协调,发挥全局性、综合性的比较优势。关注重大新战略政策,如消费升级战略、都市圈发展、国企走出去等。第四,要一张蓝图干到底,同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和分析。
杨禹在茶座尾声作小结时,围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讨论主题,概括了三个“力”——一是保持定力,包括宏观调控多年积累形成的制度定力,对中国发展大势判断的定力,把好经验坚持下去的定力;二是释放创造力,宏观调控者应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及时捕捉社会、市场、业态新变化,为宏观调控引入更多新手段、新工具;三是增强协调力,通过创新,使新时代的宏观调控更具有制度性的协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