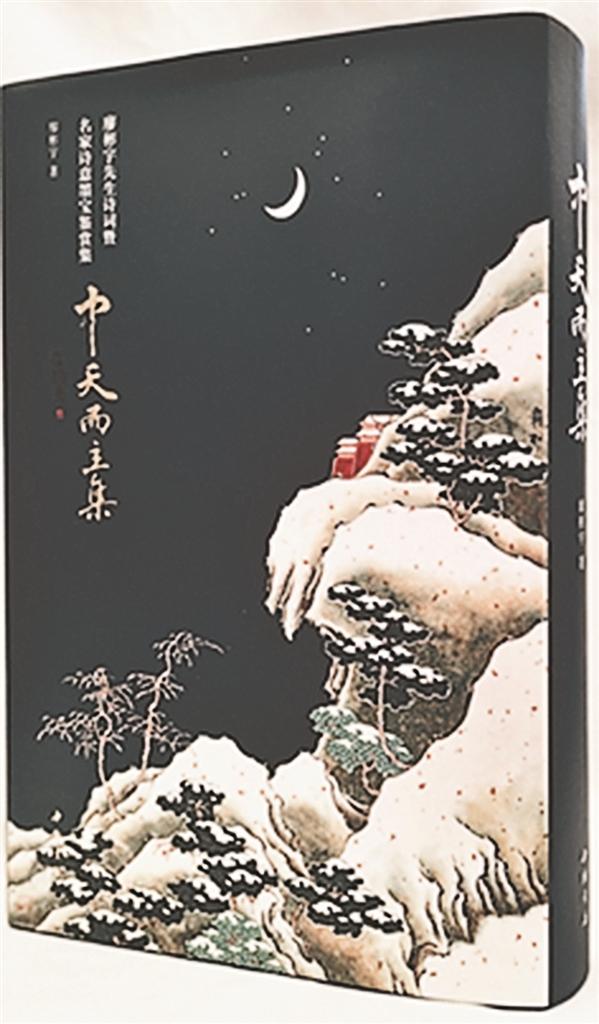写在前面:著名青年文化学者廖彬宇新出版的古体诗集——《中天而立集》,引发社会关注。究其原因有三,皆是“前所未有”:其一,该诗集前所未有地开创了诗书画合辑出版的形式。据悉,该诗集共近200首诗,由近百位中国画名家分别将彬宇先生近200首诗绘制为高质量、高艺术价值的诗意图结集出版,此种形式史上未有,古代未有或因系木刻雕版印刷的形式所限,不能复制画作使其广泛传播;近现代未有,则或因时局动荡,且绘制诗意图参与者众、工程浩大,使得作者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中天而立集》能齐聚大量优秀画家绘制诗意图,唯在新时代可行。其二,廖彬宇论诗,前所未有且系统地讲清楚了诗教为何伟大,诗教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及实用价值,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极重要的一种方式方法,为传统文化进校园找落地抓手提供了好的建议。其三,廖彬宇前所未有地阐释清楚了格律诗的产生规律,令格律诗的写作格式,从原有的知其然到了如今的又知其所以然,使格律诗的格式简单易记,便于理解。
廖彬宇治国学,始终秉承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其著作中每一个理念的提出,都有独到性思考和体系性建构的双重特点。本报特刊发著名文化学者、著名诗词评论家、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评析推介文章以飨读者。
□ 王 杰
彬宇兄《中天而立集》的出版,我很受触动,于是花一些时间阅读了诗稿,写下了这些文字。
据彬宇回忆,他生命中所接触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唐诗三百首》。在读诗、背诗的过程中,他逐渐爱上了作诗。从写顺口溜、打油诗,到写古风诗、格律诗,从“形式为诗”到“形式与内容皆诗”,这不断地变化提升过程,也正是彬宇思想境界、情怀格局、器识学养的综合提升过程。他说,为了把诗写好,曾拼命地读书、读经典、读历史,掌握词汇量,博览群书,再将所思所学变而为诗,就完成了一次创造。这既是创造性转化,也有创新性发展。把所学化为所思,将所思纳入所学,进而融入血脉精神,进行人格塑造、格局拓展、智慧发掘,便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根本价值所在。
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将诗作为一种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故名“诗教”。彬宇勤于思考,善于总结,首次提出了“诗教”这一伟大教育方法中蕴含的功能,并将之概括为“五学九维一情怀”。其中,“五学”指的是诗中包含的哲学、文学、美学、史学、音韵学,“九维”指的是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类比思维、跳跃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发散思维、战略(统摄)思维、圆融思维等九维,“一情怀”即诗中包含着悲天悯人的大担当、大格局、大情怀。同时,他写了一段简要说明,我转录于此:
诗中包含着内圣外王之道与经世致用之学,故中华民族历史上,举凡圣贤豪杰、帝王将相,大多是大诗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嗣后之刘邦刘秀、曹操诸葛,宋代大儒,甚者唐代更以诗之国度而为中华民族之盛世王朝。明清以降,朱元璋父子,刘伯温、王阳明、王船山皆诗家大宗,清之康雍乾,更是宝爱诗,清以后孙中山、毛泽东、马一浮等,皆以诗而名世、用世。诗之时用大矣哉!
中华文化重在内圣修养,己达而后达人。古琴与古诗,均尤其注重自心,关乎自在表达。所以古琴与古诗,皆是中华文化内里精神的载体,看似是无用的自娱自乐,其实正是自我修养与自我升华的自得其乐。能会得琴音诗意者,可为知己知音。这便是“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中华文化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为己之学,则恬淡冲和、谦虚中庸,光而不耀、方而不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晚成;为人之学,则自矜自伐,自赞毁他,哗众取宠,争胜逞强。现代人不明此理,不知诗之大义,以争胜逞强之心论诗,乃谓唐以后无诗,非也。持此论,则无人作诗、望而却步,诗必衰也。诗有境界高下、意趣雅俗之别,而绝无今不如昔、厚古薄今之谓。会得此理,则唐固有李杜,今亦有李杜。因而,作诗不是为了与人争,也不是为了与古人比,而是自娱自乐、自我升华,这是最为重要之处。
彬宇还将“五学九维一情怀”的理念详细做了介绍,我认为极具价值,为前人所未谈,故整理、评析如下:
哲学:站高立远,立意不凡
彬宇兄认为,写诗首先考教人的哲学修养,因而写诗能提升人的哲学修养。写诗首重立意,好诗往往源自寻常,而非同寻常。立意高,其格调便高,就能小中见大,在平常处见非常理。立意不高,无论用再多的华丽辞藻堆砌,都是或隔靴搔痒,或华而不实,或矫揉造作,或无病呻吟。
诗由文字组成,但诗又超越文字本身。“望文生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极高境界。而诗,重在意象,所谓诗意,便是蕴含着这种哲学境界。中华文化中最高的形态用“天”来代表,而天便是自然规律的总称。规律在传统中也叫作“道”,所以诗贵天真、天然、天和、天趣,还要能承载天道,这便是“文以载道”、诗曰无邪。
诗,无论是婉约的,抑或是豪放的,都有背后对生命的感悟,从生活中感悟生命,寻得生机,既是诗意,也有禅意。诗意和禅意,都是心领神会,都是妙不可言,也都是不可思议。写诗,会让人不自觉爱上思考、感悟,不自觉去饱读经典、皓首穷经,并把哲理融入诗中,自觉地完成自我的升华。
文学:驾驭文字,左右逢源
文以载道,道以弘文。琴棋书画,琴因无形无相,意蕴悠长,得太古奥义,为六艺之首;诗词歌赋,诗因其内容得意忘象,既大道至简又包罗万象,又因其形式神妙,文字精绝,音韵优美,为文学之最。
诗的文字,为雅言,也为古雅之言。古,谓其传承有自,底蕴深厚,可供考释训诂,一字而含多义,故能灵活运用;雅,即文雅不俗。所谓文言,即“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省称。诗是文言之基,也是文言之极。能写好诗,便能写好文言文;能写文言文,未必能写好诗。尤其在白话文盛行的今天,寥寥数语的古诗句,一发挥开来便能成洋洋洒洒几千几万言甚至几十万言的散文、杂文、论文、叙事文(小说)……
彬宇说,诗是文字游戏,一旦学写诗,就会爱上诗。试问,又有谁不爱玩游戏呢?人生,也是一场游戏,所谓游戏人生,很多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然而,唯有诗的游戏,让我们一开始游戏其中,最后却让人出乎其外,站高立远,超凡脱俗,成就伟大。
美学:超凡脱俗,去伪存真
彬宇说,美学是关于美的认知、审视与判断。美学的宗旨是构建美好,运用美学来实现美好。中国哲学讲天地人“三才之道”,西方哲学就讲本体、现象和作用。这两者其实是一致的。天道无形无相,却又是规律的代表,对应本体;地道有形有象有质,展现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态形象,对应现象;天地之道默默无言,但万物从中化生,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精神为无私,人戴天履地而生,具备天地的基因、天地的格局、天地的精神。天地的精神为“无私”,所以人的行为也应“无私”。无私即将至善,至善便将至美,所以叫至善至美。天的本体是真,天的德行是善,天的形象是美。中国哲学认为,合于天道者真,行于天道者善,彰显天道者美。所以美学首先是合乎道义,然后是弘扬道义。对美及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永无止境,于是产生了美学。
《易》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表明其实写诗本身也是一种修行。《庄子·渔父》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表明诗贵在真诚,不诚无物。心不静,诗也出不来。所以写诗去燥气,得静气。如果说哲学是诗的道行,那么美学就是诗的德行。写诗,可以修炼道行和德行。
诗的语言是雅言,是文雅高雅的文字语言。写诗的人,不敢说个个都口吐芝兰、口吐金玉,至少也不会口吐狂言、出言不逊、污言秽语、出口成“脏”。这便是诗,让你优雅做人,还修炼口德,还能于寻常中发现不同寻常,这便是诗的美。把这种美带到生活中,便是“诗意的栖居”。
艺术源于世俗,高于世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中国传统的诗和画,都要免俗、脱俗,这两者相合,则不俗。生活是柴米油盐,而诗不必柴米油盐;生活中都是横流的物欲和对色相的执着,而诗则追求精神气质和对空灵空性的明悟。这便是诗与画的共通处:高古、高雅。唯有高雅的追求,才能高尚,才能高贵。
史学:执古御今,活学活用
诗重用典,这考察的是一个人的史学积淀。能用典、善用典,则可以丰富诗的内涵。这体现了诗人对于历史典故的掌握与把控。诗是圣人之教,圣人之学,故而诗含蓄古雅,温柔敦厚,点到为止,艺术性表达,此为诗之德,也是人之德。诗之韵律注重婉转,诗之意境也注重婉转。这个婉转,便是“螺旋式上升”。
彬宇说,写诗,会让人不自觉地去多读历史、研究历史、运用历史。何谓运用历史?当下发生的一件小事,在诗人看来,或许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件类似的事件,把这两者关联起来,其实就是在活学活用。善于用历史来分析问题,也善于从问题中去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
音韵学:音韵格律乃传统戏曲之基
诗重韵律。韵是音韵,律是律动。诗是音乐性的语言。可以说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就产生了诗。远古人类在休息的时候,吟诗便是他们的一种娱乐,就像今天的唱歌一样。
节奏是诗的要素,最原始的诗就是具有节奏的。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和民族的不同,诗的节奏也多种多样。而但凡是节奏,就有一种回环之美,即旋律美,这便是诗的艺术形式。上古帝尧时代有老人击壤而歌,《尚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大意是说诗是歌唱的,而此种歌唱又是配合着音乐的,乐谱里的声音高低需要依照歌词的原音的高低。既然是依词定谱,这便要求原诗有整齐匀称的节奏。当然,我们今日要想详细知道几千年以前的诗的节奏是困难的,但上古时代的诗从一开始就肯定有了相当整齐的节奏。
而韵脚是诗的另一要素。可以说,从汉代到“五四运动”以前,诗几乎没有无韵者。《诗经》的《国风》《小雅》《大雅》也都有韵,唯《周颂》里有几章不用韵,也可认为此乃上古之自由诗。正是由于上古自由诗少有,从战国时代到“五四”时代又没有自由诗,可见传统诗及格律诗便是中国诗之传统。
彬宇说,诗的音韵格律其实为传统戏曲之基,传统戏曲几乎都在运用诗词吟唱之法,普遍遵循“平长仄短”的吟唱原则。古诗吟唱抑扬顿挫,以平仄关系及内容意境为基础来进行自由发挥的吟唱,则很得音乐之乐。所以诗蕴藏着诗意之美与音乐之乐。诗是艺术的至高体现与表达,因而写诗不难,但能写出好诗则尤难。真正的大诗人都是大音乐人,诗人每写一首诗,都是一首歌,他们既是词作者,又是曲作者。但一般词作者和曲作者,却往往不能互融互通。
所以说,学写诗能陶情冶性,通过吟咏诗而化烦恼为菩提,最终转凡成圣。
逻辑思维
一气呵成,上下贯通
彬宇说,写诗贵一气呵成。很多人认为一气呵成是一口气从第一句写到最后一句。其实这是误解。这个“一气呵成”,不是说时间上的短暂,才呵一口气的时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气韵流动,气脉贯通。中华文化讲究“气”,所谓生生不息之气,浩然正气,大气磅礴,气象万千都是对气的形、质、量的形容。气不能受阻、不能中断,如同中医的经络学说,一旦气脉受阻就会病变,这一口气若是断了,便会死亡。所以围棋的原理也是为了争气,还要争大气,大到气吞万里,这就有了压倒性的赢面。一旦气绝,就会输子。
因此,诗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这个逻辑是藏在跳跃背后的,既要保证跳跃性,又要保证逻辑性,这就不是一般的线性逻辑了,而是包含了线性逻辑又超越线性逻辑的多维逻辑。在逻辑思维下任君跳跃,在天马行空中依从逻辑。跳得越高越远,诗的气魄就越大,但又因有逻辑思维的串联,每一个跳跃都是活蹦乱跳,生机勃发。
也因此,诗的“一气呵成”,是语意的连贯。一首诗,写几天,写几个月,也不为过,譬如“一字吟得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灵感思维
深沉积淀,灵光一现
灵感思维又名顿悟思维。禅宗常有参禅而顿悟的案例。写诗,其实便是时常在参悟状态中,因为时刻在参悟,所以思维异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产生福至心灵之感。所以写诗需要灵感。在参禅状态下,灵感思维最为活跃。写诗,就会让我们长期处于参禅状态,灵感大增。写诗的过程往往是:触动、感动、激动。所以诗的情感表达也是让人感到共鸣的触动,让人感到情感的感动,还能让人因诗的激励而激动。
我读彬宇的很多诗,大气磅礴,可以感觉到身上升起一股股浩然之气,很鼓舞人、振奋精神。这当中就是从触动,到感动,再到激动的进化过程。
类比思维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类比思维是将多种相似的事物关联起来,归结为一类。这能迅速帮助我们概括事物的现象。在灯谜诗中时常能见到类比思维的运用。英国的培根有一句名言:“类比联想支配发明。”他把类比思维和联想紧密相联。只有有了联想才能有类比思维,不论是寻找创造目标,还是寻找解决的办法都离不开联想的作用。如彬宇在《赠李旭升大夫五律》中就运用了类比思维。第一句“木子九阳生”,木子代表草药,九阳代表纯阳之气。用中草药生发阳气,这是字面意,这句话其实又是李旭升的名字,木子为李,九阳为旭,生通假升,这就是类比关联的思维,把中草药生发阳气和中医大夫的名字相关联起来,就显得很奇妙有趣。
再如彬宇《四观经世自胜吟七律》一诗,其中有“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古来自胜皆强者,功不唐捐上九重。”人登临绝顶时,以为再无山可登,其实错了。诗人告诉读者,山登到绝顶处,别忘了人自己还是一座山,要在自己这座山上不断攀爬,不断超越自我。这首诗就是把人和山相类比关联起来了。
朱熹有名句:“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日月和人的眼睛就是类比思维,一下放大了人的格局,人的眼,就应该像天上的日月一般俯瞰众生,洞悉一切。
跳跃思维
纵横捭阖,天马行空
诗,尤其是古风,天马行空,具有很强的跳跃性。跳跃思维,能活跃思维,能灵活看待问题,使人不拘泥、不刻板,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跨越时间、空间的局限。
形象思维
图文并茂,诗情画意
汉字是表音表象的文字。在诗中,由于诗人善于组合性表达,诗的文字就能产生相应的画面感。一个“山”字,画面感不强,但一个“青山”,就产生了青山的一个画面。看马致远的名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幅孤身走天涯的画卷就非常清晰地展开在了读者的脑海中,甚至背后那种孤寂、那种悲凉感油然而生。这种悲凉感、孤寂感,便是诗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幅空旷的沙漠上升起了一道浓烟,天际还有一轮落日洒着余晖。
诗训练人的形象思维,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由此产生了诗意画。也就是画家根据诗把画面用画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能产生画面感的诗说明气韵生动,具有诗情画意。
辩证思维
平仄阴阳,互相关联
诗的形式本身就具有辩证特点,平仄的关系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尤其格律诗,从形式和内容都具有辩证性。写格律诗特别训练人的辩证思维。
彬宇说,他原本也不懂诗,念初中时语文老师说他不懂格律诗,所以教不了大家格律诗,他只告诉大家格律诗有颔联和颈联。彬宇就琢磨,诗源于易,就必然有阴阳辩证的思想。然后就把唐诗中的格律诗找出来研究里面的规律,由于他有易学基础,一下就豁然开朗,他发现古诗都是两两为一组词,两两成一组句,《易传》云:“两两相重,非覆即变”,这是易学的卦变理论,运用到了诗中来。那么格律诗呢?《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格律诗有八句,就代表八卦,代表上下左右,四面八方。
八卦是八句,分为四组,四组句就是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格律诗分四组句,不就是四世同堂吗?每一组句代表一代人,那么第一组句就是曾祖父,第二组句就是祖父,第三组句就是父亲,第四组句就是自己这一代,由此代代传承,兴家旺族,以道德传世、诗书传家的寓意。
彬宇总结说,格律诗就是一个辩证的对应系统,四组句句句对应,区别是第一组句和第四组句只是平仄关系的形式对应,而第二组句和第三组句是形式对应之外还加了内容对应。
发散思维
推演万物,一以贯之
从一点拓展出去,到线,到面,到宇宙,无限放大。这个点是一个触动点,推演开来是无穷无尽的,让人胸怀天下、视通万里。这本身也是拓展视野格局。战略思维是占领制高点、统摄万物,而发散思维则可说是战略思维的辅助,和类比思维也有相似性。
战略思维
提纲挈领,大道至简
彬宇说,诗千锤百炼,始得一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字字珠玑,一字千金,易一字而诗意全变,可谓大道至简,包罗万象。看似缩小,实是放大。以点带面,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架构多维空间。
诗训练人的战略思维,抓大放小,抓住核心少数。三言两语,便统摄无尽内涵。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诗的意义显得尤其重大。古往今来的豪杰之士,皆具有战略思维、战略眼光。而写诗,便是培养战略思维的最佳方法。
圆融思维
四面八方,外圆内方
格律诗八句,代表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每写一句,都关联全诗;每写一句都呼应其余。做格律诗,就像木工做活计,家具和木建结构均是榫卯结构,是阴阳互补关系。在木工活计中,球状鲁班锁是一种至高境界。格律诗恰如球状鲁班锁,将各种棱形、角形、方形等不规则的木物相和合而为圆球,外圆内方,代表圆满。
透过球状鲁班锁,就会明白即使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放对了地方,便都能圆融相合,放错了地方,就互相抵牾龃龉。格律诗重视规则,规范严格,稍有出律出格便是不合格或破格,正如球状鲁班锁,但凡有一点棱角突出,都不能形成球状。所以格律诗是追求大圆满的,做人也要做完人,不可有瑕疵、过错。
这也是格律诗所带给人的启发。
情怀与格局
匡时济世,悲天悯人
彬宇说,写诗是情志所发,也是平素的所思所想。写诗之人都是重感情之人,从自己的情感展开,推己及人,进一步推及天下,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情怀与格局。最终,诗的境界高下,全部体现在情怀与格局上。诗写到后面,便是激发人回小向大的发心,激发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格局。这也是诗的终极关怀。
彬宇富有创见的阐述令人叹为观止,他诚然已发现了诗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诗是如此美好——它首先是一种游戏,让你不自觉喜欢上它;然后你会不断地提升你对诗的理解和认知。随着认知的提升推动审美的提升,你会不自觉地去饱读经典,饱览历史,运用历史来镜鉴时代、当下与点滴。诗在无形中训练你的灵感思维、类比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辩证思维、跳跃思维、战略(统摄)思维以及全方位无死角思考问题的圆融思维,全面开启你的人生智慧,无限打开你的生命格局,让你改头换面,成长为心怀天下、悲天悯人的圣贤豪杰、大人君子。彬宇曾经仿照形容中华文化精神的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来形容中华文化智慧功能,也是十六字:“无中生有,有中变大,大而化之,化及天下。”我则仿照此句式,来概括诗教之精神:“寓教于乐,乐在其中。集大成者,融会贯通。”
《中天而立集》是彬宇的第一部诗集,对诗有如此深刻之见解,其诗作一定让人怦然心动、迫不及待想要去读。所谓中天而立,是中华文化特征的一个高度概括,中华文化之光,应中天而立,普照四方。中华文化的智慧,如老子“道莅天下”的赞誉,中天而立,俯瞰芸芸众生,观照芸芸众生。
我由衷地感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教诚然是孔子最为重视、最为伟大的教育方法。而彬宇则阐发了诗教的伟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无论是观照现实还是回顾历史,这都极具价值、极有意义。
(注:王杰,著名文化学者,著名诗词评论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