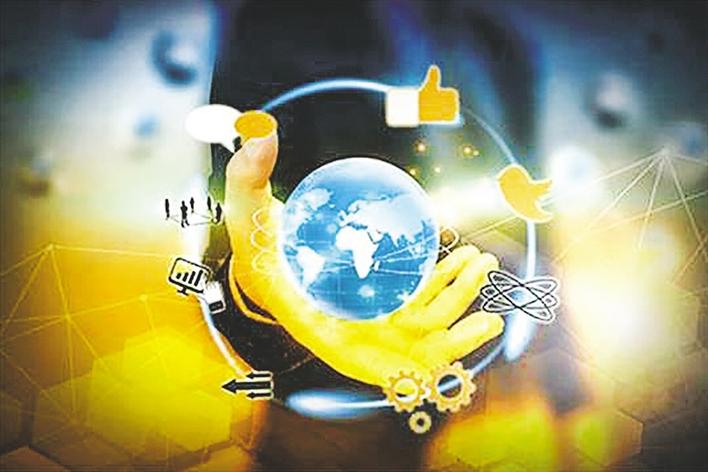□ 刘克崮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更好地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对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是服务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分三大板块:小微企业、个体自业(自雇、自就业者)和农户。从乡村角度来看,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包括四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离土不离乡创新创业主体、一般农户、贫困农户,他们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生产经营组织体系、县域镇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等三大体系的建设。支农扶弱是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使命,具体:一是改善农村县域、镇村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条件,实现县域生产和村镇居民生活条件的准城镇化发展;二是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成长、带动农户致富,加快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三是促进脱贫攻坚,扶助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谐。
农村资金供不应求,但仍大量外流。2016年,金融系统在全国近800个有存贷比数据的贫困县发放脱贫攻坚贷款2.49万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高于全国各项贷款35.5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和搬迁等贷款2.22万亿元,占比89.1%;农户贷款0.27万亿元,仅占10.9%。
县域资金供应不足。西南财大和浙江大学2017年发布的农村家庭调查相关数据均显示,在农户贷款的来源结构中,正规机构仅占20%~30%,民间借贷约占60%~70%。存款资金流失严重,2016年,央行统计的798个贫困县的银行业存贷比平均为54%,近半数的本域资金流出。
农村资金供不应求的原因:一是个体农户散、小、缺技术、信息不灵,农业抗灾力弱、附加值低,致使农村金融成本高、风险大、盈利水平低;二是农户融资缺少抵押物、财务报表,规范信息较少,难寻担保,银行放贷的信用风险大;三是商业银行逐利性强,因多种原因不断上收机构和业务;四是现行金融监管当局重风控、轻发展,责任单一,制约农村金融发展;五是农村金融组织结构、技术产品、政策支持力度和统计管理不适应客观需要。
建立新型准公共金融供给制度
解决乡村融资难,主要方式是增加金融供给,增加乡村金融供给的根本办法是建立新型准公共金融供给制度。需实行市场和政策相结合的办法,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的力度。
第一,组建准公共性草根金融机构体系。国开行、农发行等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覆盖贫困片区和县乡村基础设施、扶贫搬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立地市级分支机构,并与邮储银行一起向小微型准公共金融机构批发供资;设立或指定法定专业机构,向服务乡村小微经济体的中小微金融机构批发性供应资金、技术、担保;将农信社(农商、农合)、邮储银行打造成县域准公共金融的主力军。建立国家级农民专业银行;将现农行的“三农”事业部及所辖县级机构从农行分离出来,建立中国农民银行,或与农发行合并建立新的中国农业农民银行,也可农发行一起与开行合并;选择优秀村镇银行和优秀小贷公司分别改造组建乡村农民银行和乡村农民贷款公司,特别优秀的相关发起机构(如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可组建省域或全国性的金融集团式控股公司。
第二,建立准公共性草根金融技术产品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上述县域准公共性金融机构,应通过小组联保、现场调查、打分卡、大数据供应链等技术,发展免押、免保、免财表个人信用贷款;充分利用移动通信互联网、AI等技术手段发展省域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建设开放性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积极探索、发展省域小额信贷和其他类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以及县域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发展服务于乡村的社会征信机构和征信业务体系。
第三,建立相对独立的准公共性草根金融监管服务体系。试行存贷不出县的乡村农民贷款公司由省级金融管理部门审批和监管;试行对存贷不出县的乡村农民银行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由省级政府审批和监管;鼓励面向乡村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县域增设分支和营业网点;放宽优秀大型金融机构对优秀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批发供资的准入限制;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地域性监管,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展应以省域为限,跨省域经营要特别审批;加强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促进地方监管立法,加强地方监管部门机构编制、员工培训等方面的建设,同时,中央应给予指导和支持,帮助地方尽快适应,以便更好地完成“7+4”类金融监管任务;强化存贷比指标管理的奖惩措施,对存贷比超过100%的金融机构和存贷比不足30%、有明显虹吸作用的金融机构,由省域人民银行和银保监局联手给予激励和惩处,包括增加或减少存款网点、调入和调出存款资金、吊销存款执照等。
第四,建立准公共性草根金融双维统计制度。目前,许多普惠金融政策(如小企业贷款政策)是依据工信部等四部委实体经济划型标准制定的。同时,涉农贷款和扶贫贷款的统计口径过于宽泛、粗放、概念模糊,数字失真。许多高速公路、电厂装在“涉农”“三农”统计中;扶贫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装在“精准扶贫”中。为准确、高效地实现实体经济、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的协调,应尽快将基于实体经济划分的金融统计方法与基于金融自身业务划分的金融统计方法相结合,形成二维金融业务统计方法,并行使用,公开透明,规范严谨。
第五,建立准公共性草根金融政策引导体系。相比行政性的压任务会产生较严重的数字质量扭曲而言,发挥梯次性金融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应该更有实际效用。要实施梯次性、差异化的货币政策,根据地方金融机构扶贫、支农的深度与广度,实行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扶贫再贷款利率以及差异化的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对准公共性金融机构产品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年息24%以下保护放贷人、年息36%以上保护用款人的原则实施;实施差异性信贷规模控制政策;改单向坏账追究责任制为综合业绩评估制,对准公共性金融机构,由单项坏账终身追究责任制,改为对责任人采用优劣、双向、分时段综合评估和奖惩的办法;实行梯次性、差异化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提供5万元以下贫困农户、5万元~20万元、2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各层次农村小微经济主体贷款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异化的增值税、所得税减免政策,批发供资机构也享受同等政策;按扶贫对象层次,分档实行扶贫贷款坏账损失政府分担50%~80%的政策,遇自然灾害,酌情扩大分担比例;向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准公共性金融机构的贷款等产品提供政策性保险和担保;在界定政策适用范围时,由以批准机构划界转向以机构服务的对象、层次划界。小贷公司应享受和正规金融机构一样的财税货币政策。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学术指导小组组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