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年度“百佳”图书榜单,在其中的“10种传统文化好书”榜单上,有闽江学院教授毛晓阳教授所著的《清代贡院史》一书。这部研究科举考场的著作为什么会入选“传统文化好书”?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众所周知,科举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延续了1300多年,对隋唐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清朝末年,因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欺凌,清王朝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变革,试图挽回残局,无奈均告失败。为了推行新政,清王朝最终选择科举制充当替罪羊,1905年9月2日正式将其废除。自此以后,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都是负面居多。在范进中举、科场弊案等故事的长期渲染下,科举制更是被贴上了“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的醒目标签。
而对于科举制的主要运行场所之一的贡院,自然也难以获得好评。尽管1850年5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俯瞰福州全城时曾大发感慨,认为福建贡院“反映了中国文明中最好的一面”,但1963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对贡院评价的影响显然更为广泛。近30年来,虽然学界对科举的评价日渐公允,认为它是一种“至公之制”,甚至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但是人们对于贡院的评价依然没有太大转变,至多也只是认为贡院是科举制的具体象征。而翻阅这部《清代贡院史》后我发现,对贡院的评价竟然可以有“教育公益文化史”的视角,也就是认为贡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公益文化类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如果从职能来区分,当代中外教育公益文化的类型大致有助学、奖学、奖教3种。比如,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全国各地的教育基金会都会开展行动,向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向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班科任教师颁发奖教金,以及向因贫、因病濒临失学的学生发放助学金。而在中国古代,这些教育公益文化类型也同样存在。比如地方官学的学田,其职能是补助教师束脩、赈恤贫困学子,显然具有奖教和助学性质;又如明清书院的田产,其职能是支付院长薪酬和学生膏火,具有奖教和奖学性质。膏火的发放标准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其实就是一种奖学金。
那么,清代贡院属于这三种教育公益文化类型中的哪一种呢?《清代贡院史》告诉我们,它不属于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而应属于第四种,即“助考”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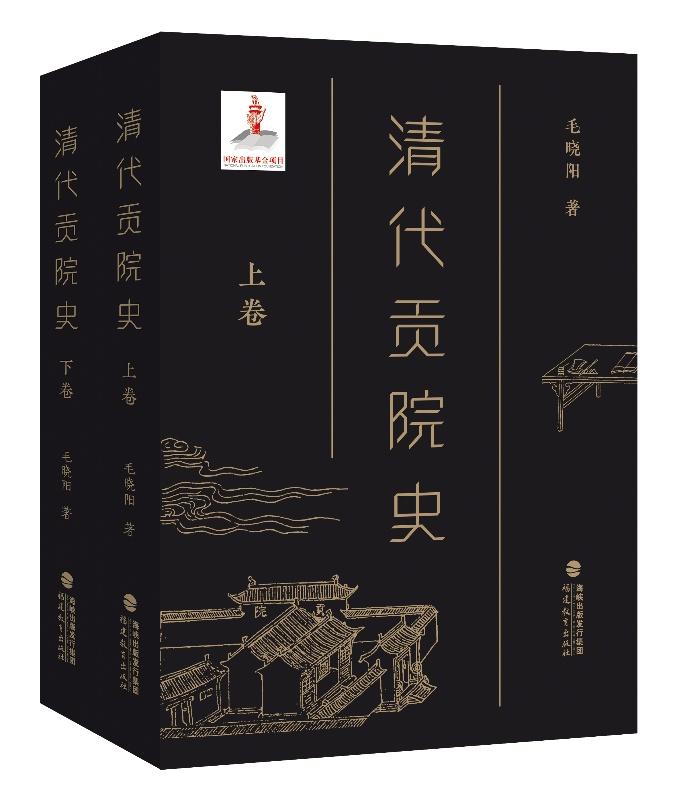
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除了比较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如省试(或会试)与解试(或乡试),较低级别的科举考试如县试、府试是没有专门的考试场所的。因为按照科场法规,宋代以来的各级各类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三年一次,每次从考试到张榜用时大约1~2个月。因此,如果建造了贡院,那么在长达30多个月的考试间歇期间,只能处于闲置状态。尤其是贡院内的考生座号区域,三年风吹日晒雨淋,不免杂草遍地、鼠雀麇集,甚至破败倒塌,每次使用前都需要修复。因此,为了尽量降低考试成本,地方官往往因陋就简,在官衙、公馆、学校、寺庙等处封锁一片区域作为考场。这种临时安排的考场,考试设施有限,往往弊窦丛生。一是桌凳均由考生自备,手提肩扛,碰撞拥挤,因而难以集中思考,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二是考试座次均由胥吏临期安排,甚至任由考生抢夺,因而难以严肃考纪,串通替考、传递抄袭所在多有,影响考试的公平公正;三是房内、檐下空间有限,部分考生不得不在露天考试,因而难以应对严寒、酷暑或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影响考试的正常举行。
正因如此,作为专门科举考场的贡院才应运而生。尤其是在清代,不仅在京师建有服务于全国会试的顺天贡院,在各省省城也建有服务于乡试的省级贡院,在各府、直隶州则普遍建有服务于学政院试和本府州府试的学政试院。即便是在最低级别的县试,也有近30%的县和散州建有县试考棚。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为了改善考场纪律、协助考生发挥、提升考试公平而建造的贡院,其修建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官民捐助,其建成后的管理人员、维护成本也都由本地士绅肩任、承担。有鉴于此,《清代贡院史》开创性地提出了“以公益求公平”是清代贡院核心文化特质的观点。这不仅突破了此前学界对于贡院的各类评价观点,更为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史开创了“助考”这一教育公益文化类型的研究。
据了解,《清代贡院史》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公益求公平:清代科举考场研究”的优秀结项成果,同时也是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成果。这部上下卷本120万字的著作也是作者继2014年出版《清代科举宾兴史》《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研究》两部专著以来再次推出的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史的全新力作,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突破。(闽江学院 陈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