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初中的时候,公社大院还在龙集老街中间,公社大院西边是农机站,农机站西边就是广播站了。听庄上老人说,龙集广播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有了。龙集广播站也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门朝北,正对着楼尚公路。院子大门旁边的石柱上,用红漆写着“龙集广播站”五个大字。广播站前面是三间办公室,后面是职工宿舍和小食堂。广播站前面的工作室放着机器:一台控制台、两台扩音机、一台大功率扩音器、一台转播器、一只唱片机、一台录音机,还有两个话筒。那时的话筒是插线的那种。
当时,公社派民兵到处架设水泥杆子,将广播线路通到下面大队、生产队。这样,广播站的广播与下面大队的大喇叭、各家各户的小喇叭(广播)连成一个整体。那时,下面的大队部、乡下庄子的庄头都安装大喇叭。农户每家屋里都安装小喇叭。各家的小喇叭,形状像一只大碗,外面罩着一个正方形木盒子。木盒上刻着五角星图案。家用的小喇叭,块把钱一个。那时农村的小喇叭,采用单线传输。各家的小喇叭从外面的广播线上接进一根天线,再从小喇叭里接出一根地线,插入下面的地里。这样,广播站广播时,各家的小喇叭就会发出声音。有时,天气干燥,小喇叭声音变小,听不见,父亲就叫我拿水瓢舀一瓢水,往插地线的地方浇。泥土湿润了,不一会,小喇叭声音就变大了。夏天打雷的时候,父亲就叫我把小喇叭的地线拔掉,防止雷电烧坏小喇叭,引起火灾。后来,家里条件好了,父亲买了小开关,装在小喇叭的地线上,节目来了,打开地线的开关,小喇叭就响了。夏天雷雨天气,父亲就把地线上的开关关掉,这样就安全了。当时广播站职工不多,只有四五个人。站长姓赵,杨洼人,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腰有点驼。他穿着得体,梳洗整洁,上衣口袋上总是插支钢笔。他性格活泼,沟通能力强,广播站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些年,公社如果有事,就找赵站长通知。每次广播突然停了下来,这说明公社有通知了。这时,赵站长拿起话筒“喂、喂”两声,下面就开始播送一条通知。因为赵站长经常播送通知,社员们都习惯了他的声音。偶尔赵站长有事外出,就找其他人代替。其他人播送通知,大家都不习惯,相互打听赵站长怎么了,去哪了。

广播站还有一个姓侯的,龙西人,个头也不矮。他穿着朴素,整天穿着劳动布裤褂。他老实得像一头老黄牛,每天闲不住手。每天广播前,他提前开机、预热机器,打开向下面大队广播的线路闸刀,然后进行预报节目:“龙集人民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六点转播泗洪县人民广播站节目……”接着,他将插孔插到县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上。每天广播节目结束,他及时关上机器的开关。河口的小赵,性格内向,整天只知道干活。他负责广播线路的架设、检修和维护。他还负责机器的养护和维修。如果机器出现故障了,自己修不了,他就请县广播局的师傅来修。广播站赵站长、老侯、小赵,都不是公社的正式干部,他们都拿大队的工分,不过公社有时也给他们一定的补贴。广播站有时也会从附近大队请两个播音员来。这些播音员有男有女,都是高中毕业生,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能讲会说的,都能自导自演、自己编排。他们的普通话说得稍微好一些,不过也经常夹带些龙集方言。这些播音员是广播站临时请来的,他们拿生产队的工分,在站里是没有编制的。他们虽然是临时的,但给人的感觉是正规的,多少带有点神秘感。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高,受人尊重。广播站还有十几个通讯员,分布在各个下面大队。通讯员与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劳作,战斗在田间地头。他们在劳动现场采写“抗旱排涝”、“抢收抢种”等方面的新闻,采访“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写成稿子当日傍晚就送到公社广播站广播,有时还报送到泗洪县广播局。广播站清晨开播、晚间关机,遇到突发事件,或台风、暴雨、霜冻等不测气候,还会临时开机播音。所以广播站需要有人全天候在岗。有一年麦口,突然有台风,为了防止集体财产受损失,半夜零时,赵站长打开机器,向全公社广播,提醒大家抢收好社场上的麦子。广播站人手不多,但是事情不少,滑(全)是播音,就有头十个小时。广播站每天按固定时间分早、中、晚三次广播,早上从五点五十到九点,中午从十一点到下午两点,晚上从六点半到十点。碰到农忙,或特殊时期,早晨要提早三十分钟播音,晚上要延长广播结束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要安排很多节目。每天在黄金时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时,播音员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现在播送报纸摘要节目”……在那个年代,农村的小广播是唯一的传媒手段,让农村人知晓国内、国际的新闻,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完新闻联播后,还播放样板戏、革命歌曲、相声、评书等节目。那年代的戏剧,主要是《沙家浜》《红灯记》《龙江颂》等八大样板戏。在那样的物质匮乏时代,能听上戏剧、相声、评书,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晚上八点半,“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后,县广播站还有农业农村专题节目,以普及农业生产知识为主要内容,当时有化肥、农药的使用常识,农作物新型品种的推广和普及等。“天气预报”节目,是大众喜欢关注的节目。人们根据天气预报安排农业生产。广播站有时还要报道龙集公社的本地新闻,宣传龙集当地的好人好事。公社领导经常利用广播,召开全公社干群广播大会,传达泗洪县委、县政府的会议精神,介绍龙集当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播发各类通知,安排“春耕”、“双抢”等活动,指挥生产。那时农村人大多没有手表、闹钟,平时人们靠看太阳、月亮位置,或凭经验判断时间。广播每天早、中、晚准时播放,成了乡下人日常生活的“钟表”。从早晨六点开始,到晚上十点结束,广播发出“滴、滴、滴”三声后,“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几点整!”人们根据广播的报时,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清早,广播播放了《东方红》乐曲。大家都知道天亮的,现在五点五十了。《东方红》乐曲之后,播音员对着话题播报:“龙集公社广播站,今天开始第一次播音,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早上好!今天是x月x日,农历x月初x,星期x,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节目。”这时人们开始起床,刷牙的刷牙,洗脸的洗脸。洗漱完毕,大人去湖里干活,孩子背书包上学。中午,“广播响了!”大家知道十一点了,天中了,扛着锄头,拎着镰刀回家做饭。傍晚,“广播响了!”大家知道六点半了,天晚了,可以烧晚饭了。夜晚,广播里《国际歌》响起。这时播音员说:“今天广播到此结束,明天再见。”大家都知道十点了,可以洗脚、上床睡觉了。三四十年过去了,随着收音机、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广播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广播站这个单位也就解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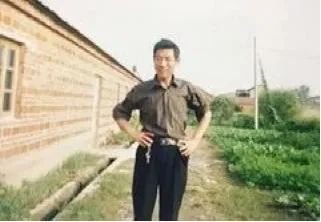
徐宜业,江苏省泗洪县龙集镇人,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被评为镇首届名师、县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县政府优秀教育工作者、县优秀班主任、市语文骨干教师,主持多项国家、省市级课题并结题。作品发表于各级各类报刊平台。